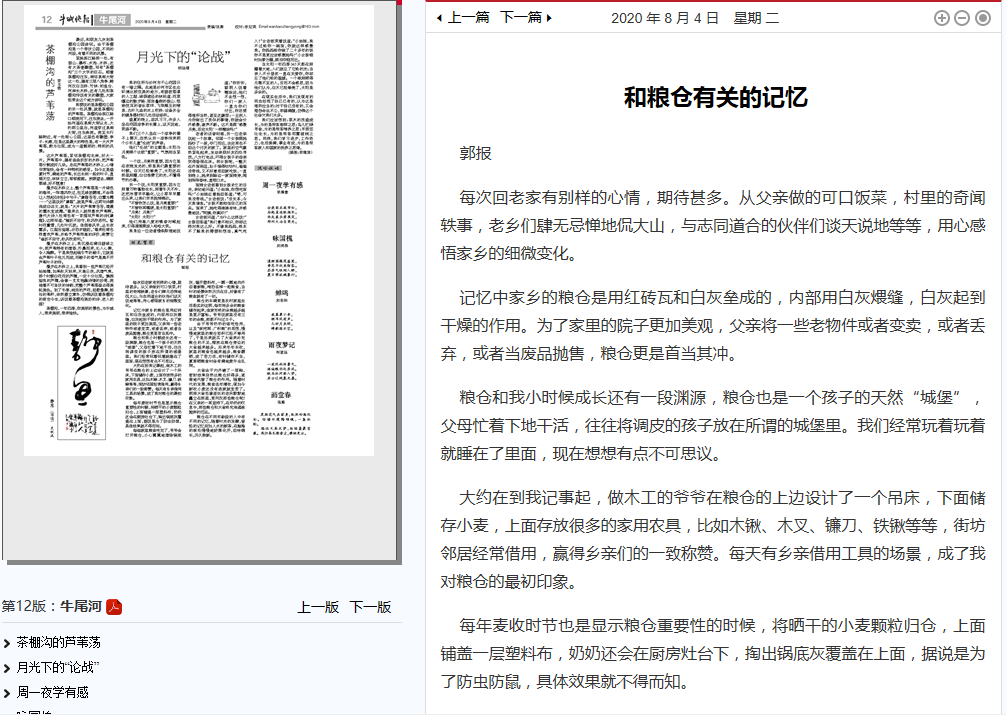
每次回老家有别样的心情,期待甚多。从父亲做的可口饭菜,村里的奇闻轶事,老乡们肆无忌惮地侃大山,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谈天说地等等,用心感悟家乡的细微变化。
记忆中家乡的粮仓是用红砖瓦和白灰垒成的,内部用白灰煨缝,白灰起到干燥的作用。为了家里的院子更加美观,父亲将一些老物件或者变卖,或者丢弃,或者当废品抛售,粮仓更是首当其冲。
粮仓和我小时候成长还有一段渊源,粮仓也是一个孩子的天然“城堡”,父母忙着下地干活,往往将调皮的孩子放在所谓的城堡里。我们经常玩着玩着就睡在了里面,现在想想有点不可思议。
大约在到我记事起,做木工的爷爷在粮仓的上边设计了一个吊床,下面储存小麦,上面存放很多的家用农具,比如木锹、木叉、镰刀、铁锹等等,街坊邻居经常借用,赢得乡亲们的一致称赞。每天有乡亲借用工具的场景,成了我对粮仓的最初印象。
每年麦收时节也是显示粮仓重要性的时候,将晒干的小麦颗粒归仓,上面铺盖一层塑料布,奶奶还会在厨房灶台下,掏出锅底灰覆盖在上面,据说是为了防虫防鼠,具体效果就不得而知。
每每家里粮食吃完了,爷爷会打开粮仓,小心翼翼地清除锅底灰,揭开塑料布,一瓢一瓢地向外舀着新粮,唯恐丢掉一粒粮食,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,好像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。
粮仓的丰满更是农村家庭生活殷实的证明,每年将多余的粮食储存起来,谁家年终的余粮越多越是显示富裕。爷爷说家里没有三年的余粮,那都不叫过日子。
由于爷爷奶奶的省吃俭用,以及“深挖洞、广积粮”的思想,慢慢地家里的粮仓容积已经不够用了,于是后来就买了大瓮来补充粮仓的不足,摆放在粮仓旁边的大瓮越来越多。后来年年丰收,家里的粮食也越来越多,粮食翻晒,成了苦力活,有时储存不当,夏季晒粮食时会有满地麦牛虫乱爬。
大瓮由于内外镀了一层釉,密封效果自然比粮仓好得多,逐渐地代替了粮仓的作用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粮食连年增收,现如今新收小麦还没有进家就变卖了。两排大瓮也像退伍的老兵默默地矗立在那里,更何况那些粮仓呢!在父亲的一再坚持下,在奶奶的叹息中,那些粮仓和大瓮终究难逃被抛弃的厄运。
粮仓在不同年龄段的人中有不同的记忆,随着时光的发酵,曾经的记忆宛如入水的新茶,在脑海的深处慢慢地舒展化开,回味绵长,历久弥新。
牛城晚报 8月4日 牛尾河 郭报